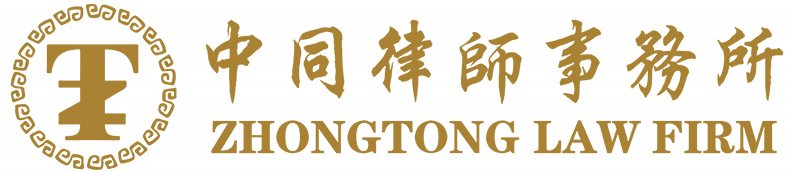推荐阅读
Recommended reading

文章来源:北大法宝
【作者】:王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声明】:本文为原版,简洁版发表在《检察日报》2019年4月2日第三版,题目为:《“非法性”是确定融资活动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之间,行为人均以筹措资金为平台和载体,但是两者的法律性质却截然相反,后者被冠以否定性评价的标签。由此可见,“非法性”是区分融资活动的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也是融资行为的刑事法律风险边界。有鉴于此,在我国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四个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2011年)是专门针对该问题而颁布的,“两高一部”在2014年3月和2019年1月联合颁行的两个“意见”的第1条,也都是为了解决“非法性”的认定难点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发布11项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执法司法标准中,开宗明义地首先就要求严格把握非法集资“非法性”的认定。然而,对于“非法性”这个最为关键性的本质特征之认定问题,在我国规制非法集资的法律规范中却多次发生变化。可以说,在政策和立法层面,“非法性”起到划定刑事法律界限的功能和作用,但这仅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性问题,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非常容易导致罪与非罪的法律界限呈现模糊的状态,这会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弹性和解释空间,也为滋生新的“口袋罪”奠定了土壤或者温床。
正是基于此,司法机关在打击非法集资的活动中,当实在无法找到准确的罪名予以适用时,很自然地就会将定性的难点都放在这个“筐子”内来加以稀释,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沦为非法集资犯罪体系中“口袋罪”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严格把握正当融资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界限,正确地把握非法集资犯罪中“非法性”的认定问题,防止司法机关滥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需要我们在教义学上把脉“非法性”本质特征的流变,并且对“非法性”的认定标准、内涵和认定程序等第二层次的操作问题进行研究。
一
一元标准:“未经批准”的形式标准
从我国规制非法集资法律规范的发展变化看,“非法性”的认定标准在早期一直被限定在“未经批准”上。例如,在我国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79条中,对于“非法性”的使用术语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鉴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发生转变,在2003年修正的《商业银行法》第81条中,则被修改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由此可见,在关于非法集资的最早司法解释中,“非法性”是被限定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这个唯一的形式认定标准上,而且对于批准的主体,采用高度概括的术语。
二
二元标准:形式标准+实质标准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在1999年1月下发《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为《取缔通知》),在第1条明确规定了非法集资的四个特点:“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的集资;
(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还包括以实物形式或其他形式;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4)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审理非法集资刑案的解释》)中,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基本上保留了上述《取缔通知》中非法集资的四个特点,但也有所发展,这具体表现在将《取缔通知》中规定的“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和“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两个原本单独并列的特点,共同合并为“非法性”认定的选择性要件,只要具备其一即可定性,不再要求认定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对比可见,在沿用中国人民银行《取缔通知》的行政规定的基础上,司法解释将过去“非法性”的一元认定标准,修改为二元标准,这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形式认定标准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这是“非法性”判断的通行标准和具体化规定,不仅便于司法操作,也契合于我国对吸收公众存款实行审批制的法律规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考虑到将非法集资的定义仅仅落脚在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存在诸多局限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难以满足新形势下打击新型非法集资活动的需要。例如,未经批准只能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审批而未经审批的非法融资行为,包括合法借贷、私募基金等在内的合法融资活动,则无需有关部门批准;获经批准并不一概合法,违法批准、骗取批准的集资行为仍属于非法集资;对于法律已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没有必要考虑是否批准的问题;对于以生产经营、商品销售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是否批准不具有直接判断意义。因此,“非法性”包括未经批准,但不限于未经批准。换而言之,如果将“非法性”的认定局限在单一的形式认定标准,则不能满足打击非法集资的实际需要,这是产生二元认定标准的现实驱动力。
2
实质认定标准
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即将“挂羊头卖狗肉”的集资行为,也纳入“非法性”的认定范围之列。如前所述,该司法认定标准源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取缔通知》,但在用词上有所改变,这特别表现在将“卖狗肉”的目的行为,从“掩盖非法集资的性质”改动为中性词语“吸收资金”,舍弃了否定性评价的用语,这值得商榷。由于该标准属于实质性认定范畴,即对此标准认定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批准,而在于是否以生产经营和商品销售为名,行非法集资之实,故其外延更为宽泛。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说明中强调,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实践中应当注意结合《审理非法集资刑案的解释》第2 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等关于非法集资行为方式的规定,根据非法集资的行为实质进行具体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该实质标准的弹性和模糊空间很大,非常容易成为认定“非法性”的“黑洞”。换而言之,许多司法人员在无法以形式标准认定非法集资的“非法性”时,则转向于以该实质标准作为打击入罪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废弃了“非法性”的关键认定门槛标准,从而导致打击非法集资范围的任意扩大化。可以说,这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沦为非法集资犯罪体系中“口袋罪”的根本原因,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
三
二元标准的将来发展
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条中,非法集资被定义为:“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或者超过规定人数的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的行为。金融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细分可见,“非法性”的认定标准将再次得以发展,它被界定为以下两个类型。
1未经依法许可
对比而言,这基本保留了现行司法解释中的形式认定标准,但将其中的“批准”一词,修改为“许可”。在外延上,“许可”要宽泛于“批准”。例如,在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中,事前备案是指完成备案登记手续后方可开始活动,体现了审批制。这相当于将未经依法事前备案的集资行为等纳入“非法性”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非法集资的打击范围。
2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废除了现在司法解释中的“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之实质认定标准,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值得充分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该认定标准实际上是套用了《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关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非法性”之用词,其法律外延依然很宽。本文认为,这依然需要加以限缩,即借鉴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将“非法性”一词中的“法”之范围,仅限定在“违反国家规定”,即“国字号”的层面上,防止行政主管部门对金融部门利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行政规章之介入,从而体现出防止非法经营罪在司法中滥用的成功范例。对比可见,这也有当前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文件予以支持。
例如,《审理非法集资刑案的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从法律措辞看,该解释采取的是绝对性立场,完全排除“国字号”之外的部门规章作为认定“非法性”的依据。后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发布11项关于保护民营企业发展的执法司法标准中,在严格把握非法集资“非法性”的认定时,则要求应当以商业银行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同时可以参考中国人民银行、银保会、证监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由此可见,与《审理非法集资刑案的解释》相比较,该“司法标准”采取的是折中立场,在基本底蕴上是以“国字号”的法律法规作为“非法性”的认定依据,但也有所松动,规定“可以参考”部门规章。
在上述“司法标准”的基础上,“两高一部”在2019年联合颁行《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第1条关于非法集资的“非法性”认定依据问题中,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时,“应当以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对于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仅作原则性规定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予以认定。”对比可见,该“意见”是继续采取折中的立场,但是也有所发展,把“可以参考”部门规章的前提限制在“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仅作原则性规定”的时候。
综上所述,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性”本质特征的认定标准,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和法律规范的变化频次很高,内容的修改幅度也较大,由此也体现出“非法性”认定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难点问题。
四
“非法性”认定的行政程序前置之流变
对于涉嫌非法集资案件性质的认定,国务院在2007年颁布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中,要求按照以下分工进行:“1、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策界限清晰的,由案发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当地银监、公安、行业主管或监管等部门进行认定。性质认定后,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进行查处和后续处置。2、重大案件,跨省(区、市)且达到一定规模的案件,前期调查取证事实清楚且证据确凿、但因现行法律法规界定不清而难以定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后按要求上报,由联席会议组织认定,由有关部门依法作出认定结论。”这是在行政程序方面,对“非法性”的认定予以界定。
在打击非法集资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经常遇见一个难题:对于民间集资行为,很多是在当地政府的长期默许和同意下进行的,甚至屡屡发文件鼓励民间融资,从而导致集资行为的泛滥。当集资行为“崩盘”之后,为了推卸自己的监管失职行为,当地政府的官员往往不对非法集资的性质予以认定,甚至竭力推托或者拖延,从而导致非法集资案件无法进入刑事追究程序。针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专门颁布《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问题的通知》,规定:“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案件进入刑事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审判。法院应当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并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在有关部门关于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行政认定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由此可见,对于“非法性”认定的行政程序前置问题,该“通知”是采取否定的立场,以便保证对非法集资行为的及时打击。
在2014年,“两高一部”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中,在基本原则方面,继续否定行政程序前置,规定:“行政部门对于非法集资的性质认定,不是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行政部门未对非法集资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案件事实的性质,对于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可参考有关部门的认定意见,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性质认定。”但是,考虑到非法集资属于行政犯的范畴,牵涉面很广,如果在司法认定时完全排除有关部门对“非法性”的认定意见,并不现实和可行,故在该“意见”中对否定行政程序前置的立场有所松动,规定“可以参考”行政认定意见,并且把认定范围限定在“案情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